【连网】 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这本书很奇特,前半部分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·福山的访谈录,中间夹放了法国摄影家奇妙的摄影作品,后半部分则是命名为《反乌托邦》的诗集。其实,我对福山的兴趣要远大于诗,但福山的政治观点适合慢品,写出来则枯燥无味。所以,本篇文章专门以《反乌托邦》的诗集来引谈一些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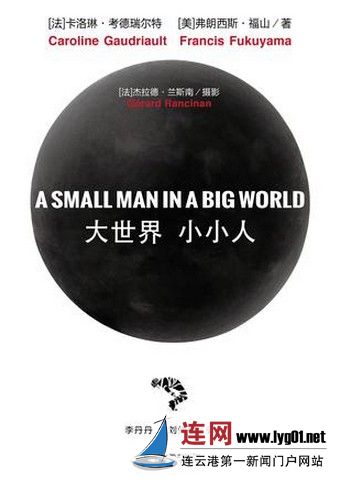
当我们谈论诗歌的时候,诗去了哪里
本书中有首叫《你的小皮鞋》的诗,“那么,小人儿,你曾经跋涉万里/你不经常折回/就好像道路没有尽头/你任由别人拉去,玩起了寻宝的游戏/并不晓得到底谁引领了你。”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诗歌的概括,诗歌的发展是条历史的长河,但中国古诗自清之后便几乎与现代中国彻底告别,简直可以称为“灭绝”了。现代人写的古诗多不堪入目,或不重格律,或浅无意蕴。
前些日子北大的9位教授“限韵作诗”,读来令人汗颜,这更加落实了古诗写作之不易。诗的写作需要情境与文化环境,如果脱离文化的大环境去强写,自是难以写出令人认可的诗作。现代语言环境下,再写古诗,便有了文化上的隔阂,再大的学问也不比古人。由此,才会有了现代诗的春天,也由此在当今,诗人几乎限定在现代诗领域。
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的诗都是现代诗,这是毫无疑问的,毕竟它是译作。但译者之一刘仲敬先生是通文言的,也未敢于去尝试将现代诗反译成文言或古诗。其实译诗也存在涵义递减的现象,不同的人译出来的诗存在着不同的意蕴,诗歌大家如果有翻译的能力,其译诗自是更加耐读。冰心在《我也谈谈翻译》一文中说,“我只敢翻译散文或小说,而不敢译诗……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化形式,因此译出时,即使不失原意,那音乐性也没有了。”其实,后来,冰心还是译了许多诗的,读起来非常有味道。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的诗译水平不能说差,但远没有达到最好的水准,或许这与两位译者的诗学修养有关,译诗实在太难。
在英语语境下,一个词读来会有美的感受,翻译成中文则可能乏味;同理,中文翻译成英文也会失去中国文字的魅力。有时候,诗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,每翻译一回,便失掉原意一些。本书中有篇诗作《无限大》,其中几句翻译成的文字是“在这个令人晕眩的空间,这些站立的小人儿,相互安抚、相互慰藉”,读来不是诗的语言,甚为可惜。
现代诗的自我情结
作家王路认为现代诗人有文饰倾向,“你要把诗写得好,你得过分注重自己的情绪和觉受,你要变得敏感,甚至极端,诗才有震撼力,才能摄人心魄……重情绪而轻智识,重自身而轻外物”。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。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将诗部分命名为《反乌托邦》本身便有种癫狂的气质,现代诗人是不屑于与主流为伍的。
在本书《世界剧场》一诗中,这样写道:“那不面向任何地方的窗子/那些朝着空洞开启的房门/整个的、脆弱的城市/它们自生自灭/哪来的念头,认为世界围着你转动?”写得直白,直抒胸臆,这是现代诗的写法。
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时代,还是受到中国古诗“发而中节”这类含蓄蕴藉精神影响的。到了现在,则完全与世界上的一些主流写诗习惯并线了。最近非常火的诗人余秀华被冠以“脑瘫诗人”,这是一种歧视,但其作为诗人的成名、火爆及被流传,诗写得自然是好,同样“注重自己的情绪和觉受”。她的诗《我爱你》里的词句便直白到毫不掩藏自己的内心,“巴巴地活着,每天打水,煮饭,按时吃药/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,像放一块陈皮/茶叶轮换着喝:菊花,茉莉,玫瑰,柠檬/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/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/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”。
为什么要提余秀华呢?因为我觉得,如果她懂得英文,如果她可以翻译诗,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由她来翻译会是另外一种味道。本书中诗篇《你乳白色的肌肤》:“你用饱含期许的目光凝视我/你牵着我的手让我为你引路/我知道你依赖我/如此强烈的责任/你对我微笑,眼睛死命地盯着我”。原文肯定要有味道得多,翻译过来便失去了诗的力量,而像余秀华这样的诗人,她懂得诗人的内心,翻译起来的话,应该会更加重视诗神而略过诗形。
在这个时候,我就怀念古诗,如同王路一样。他举了郭沫若与薛昭蕴的区别。郭沫若写《天狗》:“我是一条天狗呀!我把月来吞了,我把日来吞了,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,我把全宇宙来吞了。我便是我了!”这是现代诗。薛昭蕴《浣溪沙·红蓼渡头秋正雨》:“红蓼渡头秋正雨,印沙鸥迹自成行,整鬟飘袖野风香。不语含嚬深浦里,几回愁煞棹船郎,燕归帆尽水茫茫。”这是古诗,“时时刻刻,都有克制的功夫在。极激烈的情绪,以极平淡的语句出之。读者必须穿透这种平淡的语句,才能和作者相见,体会作者的内心。”
式微的现代诗何时再起航
如同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里写得一样,现代诗人“从容地走出大门,出来时面带满足而愚蠢的微笑”。这是现代诗不被大众认可的困境。诗人几乎成了负面词汇,这令人感到不安。诗人本该是文化的试验田的,现在却成为过街老鼠一般。所以,我极愿意看到诗人再多一些,现代诗(尽管总过于直白)再多一些,哪怕像“梨花体”这种被大众嗤笑的试验再多一些。
余秀华说,“我从来不想诗歌应该写什么,怎么写。当我为个人的生活着急的时候,我不会关心国家,关心人类。当我某个时候写到这些内容的时候,那一定是它们触动了,温暖了我,或者让我真正伤心了,担心了。”她告别2014,“下一个春天啊,为时不远/下一个春天,再没有可亲的姐姐遇见/但是我谢谢那些深深伤害我的人们/也谢谢我自己:为每一次遇见不变的纯真”。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则这样鼓励人们,“路途没有终结/鼓起勇气/追随你的影子/朝圣的路上你并非孑然独行”。我相信,不论是余秀华,还是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的作者,都在鼓励诗人多向前走一些,再多走几步,不要太在意世界的看法。
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余秀华成名后的场景。“当地有关部门也来了,慰问,与媒体对接,试图借余秀华打造‘乡土作家群’的城市名片。此外,有公益机构提出为她募捐;有自称她高中恩师的人与记者联系,要与她见面;有此前关系不好的诗友上门,提出做她的经纪人;还有隔壁村村民,带着研究生女儿,来跟她切磋……对于这些,余秀华几乎都拒绝了。”幸好她拒绝了,作为一个诗人拒绝了。现代社会容不下诗人的成名,尽管诗人的稿费是按字算的。
我希望诗人们可以像余秀华一样排除干扰,“保持着惯有的警惕”。也希望像《大世界,小小人》里写的那样,“我可以体会到妒忌和贪婪/然而,我并非有罪/我可以感受到反感甚或恶意/然而,我并非有罪/无论如何,我是人。”是的,无论如何,作为诗人,在朝圣的路上,你并非孑然独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