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记者 杨锐冰 张晶晶/文 牟进勇 樊晓姝/图)父亲早逝,她立志研制“百姓用得起的特效药”,来自南城街道九岭社区的郑惠文今年572分考取南京中医药大学;在灌南县李集镇久安村的一家小店里,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腿脚不便的父亲守着微薄生计,18岁的刘文文以582分的高考成绩考入扬州大学;父母在他不到1岁时离异,父亲辗转工地打工,毕业于灌南高级中学的严苏宇今年546分考取江苏理工大学;三间瓦房静立在玉米地旁,68岁的父亲周良岗忍着病痛割净门前杂草,屋内霉味隐约,刚考上重庆师范大学专升本的周小洲站在为5000元本科学费彻夜难眠……
这是四个用读书劈开荆棘的故事,更是四盏在泥泞中依然灼灼燃烧的星火。
父亲早逝,她立志研制“百姓用得起的特效药”
郑惠文572分考取南京中医药大学

深夜,当同学们早已进入梦乡,17岁的郑惠文还在昏黄的台灯下啃着物理题。草稿纸堆了半尺高,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“只要多学一点,离梦想就更近一点。”
10岁那年,父亲因病去世。那时候,小小的郑惠文就萌生学医药的念头。7年后,这个念头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今年高考,郑惠文以572分的成绩被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制药专业录取。她选择这条路的理由简单而沉重:“我想研究出价格更亲民的特效药,不让更多家庭经历我家的痛苦。”

推开位于南城街道九岭社区郑惠文家的门,扑面而来的是生活的重压与不屈的生机。79岁的爷爷和76岁的奶奶年迈无劳动能力,母亲杨利是全家唯一的支柱,做着保洁工作,每月收入仅2000余元。这个七口之家,有五人吃着低保,每月2000多元的低保金是重要的补充。除去四个都在上学的孩子——读初中的妹妹和读小学的双胞胎弟弟——学费生活费压得这个家捉襟见肘。
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郑惠文早早体味了这句话的滋味。父亲去世后,她瞬间长大,学习之余的所有精力都用来帮母亲分担。这个暑假,当同龄人憧憬着难得的放松,她却忙着做家教,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她不仅为自己积攒大学学费,还主动担起为弟弟妹妹辅导功课的责任。“姐姐就像我们的小老师,”妹妹说,“但她对自己最严格。”

生活的风霜从未磨灭她眼底的光,反而铸就了她超乎常人的韧性与清醒。谈到学习,郑惠文没有太多“窍门”,她的经验朴实得让人动容:“就是多跟着老师的节奏,然后拼命找自己的不足。”高中物理曾是她最大的“拦路虎”,成绩一度在三四十分间徘徊。换作他人,或许早已放弃,
但她偏不。
无数个夜晚,家里那盏旧台灯总是亮到很晚。她埋头于一道道令人头疼的物理题,网上查找资料、反复观看教学视频、自学消化。演算的草稿纸堆起半尺高,额头上常因专注而沁出细密的汗珠。“那时候就想,我不能输,我得多学一点,再学一点……”回忆往昔,她语气平静。
最终,她的物理成绩在高考时突破了70分。这30分的跃升,背后是无数个夜晚的孤灯奋战,是一个寒门学子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坚定信仰。
她清楚地知道,这条路很长,本科仅仅是个起点,“我今后还要继续读研。”深入科研领域,去真正触碰那个“研制百姓用得起的特效药”的梦想。郑惠文用她的故事告诉世人:生命予你以苦难,你却报之以歌,用坚韧作谱,以奋斗为词,终能响彻云霄。她不仅为自己挣来了一张挣脱困境的门票,更矢志为无数像她曾经一样无助的家庭,点燃一束科学带来的、充满温度的希望之光。
残疾父亲开小店托举梦想
刘文文582分考取扬州大学

在灌南县李集镇久安村的乡间小路上,一间没有招牌的乡村小店藏在绿树掩映中。门口斑驳的墙面上,“刘金全商店”几个红色油漆字是它唯一的标识——这里售卖着烟、水和饮料,顾客多是本村乡邻,生意清淡得几乎不挣钱,却是刘金全和儿子刘文文相依为命的“根据地”。
“爸爸的小店挣不了多少钱,奶奶93岁了,大爷叔叔们轮流照顾。”刘文文坐在板凳上,轻声说着。
2020年,在他初一的那段日子里,父母因感情不和结束了婚姻。父亲刘金全排行老五,从小因小儿麻痹症落下腿脚不便,只能守着这间小店维持生计;母亲则在疫情期间远赴浙江义乌打工,日子过得并不轻松。

“妈妈再婚又离婚,却从没断过我的生活费,每个月1000元到2000元准时到账。”刘文文记得清清楚楚,得知他考上大学,母亲特意凑了5000元学费,还买了新手机让他带到学校,“她说在外打工再难,也得供我读书。”
这份来自父母的爱,成了刘文文成长路上最暖的光。在灌南惠泽高级中学的课堂上,他永远是坐得最直、听得最专注的那个。成绩单上,数学118分、物理90分的高分凸显理科优势,但75分的化学成绩让他总念叨:“这科没考好。”
谈及学习方法,他腼腆一笑:“上课跟着老师节奏走,课后再找练习补薄弱处。”没有补习班,没有优越环境,他就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写、一道题一道题啃,“爸妈都不容易,我得靠自己。”
今年夏天,刘文文582分考取扬州大学。尽管专业被调剂到车辆工程,这个从小在生活里“闯关”的少年却格外珍视这份礼物。“拿到通知书那天,我偷偷红了眼眶。”他坦言,生活的拮据没消磨志气,反而让他更早懂得努力的意义。
9月6日就要踏上去扬州的报到路,刘文文对未来已有规划。“我想转去电气自动化专业,听说这个专业好就业,未来还想考研。”他望着小店门口的乡间小路,眼神坚定,“专业调剂是暂时的,只要够努力,总能靠近目标。”在这间承载着生活重量的小店里,少年的求学梦正迎着阳光,悄然生长。
严苏宇546分考取江西理工大学
零售店收银台后的“智能建造”梦


夏日的上海零售店里,空气黏湿闷热。18岁的严苏宇站在收银台后,熟练地扫码、装袋、收款。
在灌南县堆沟港镇刘集村,一条蜿蜒的村路通往老屋,门槛被岁月磨得发亮。这是一个被生活拉扯着的家。不到1岁时,父母离异。他的童年被一分为二:在安徽阜阳,跟着外婆和母亲生活,记忆里是母亲在装修公司早出晚归的背影;小学六年级,他回到灌南,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,父亲四处辗转江苏各个城市的工地打工,年收入仅一万五千元,是这个家的经济支柱。
高中三年,在灌南高级中学的教室里,他把自己“钉”在了书桌前。没有琳琅满目的课外辅导书,但他有错题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;没有昂贵的学习设备,但他有不肯向难题低头的倔强。知识,是他唯一能紧紧抓住、改变命运的绳索。
今年高考,他为这个漂泊分散的家带来了最坚实的光亮——以546分的成绩,被江西理工大学智能建造专业录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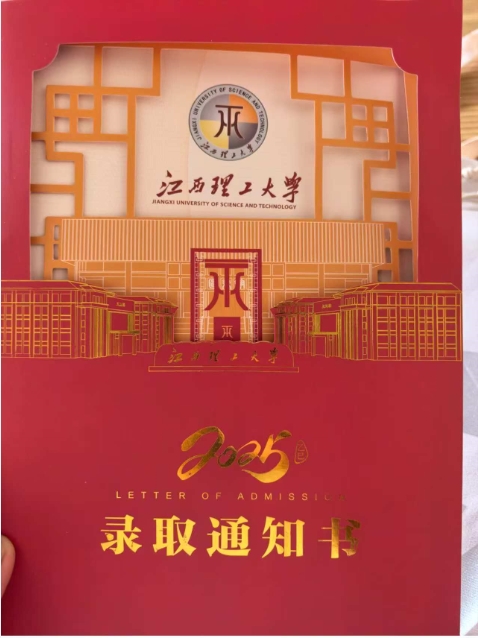
他选择的智能建造,是一个用科技与智慧重塑建筑行业的前沿领域。对于严苏宇而言,这个选择包含着更为具体和温热的意义——他来自一个被距离隔开的家,他见过母亲在装修公司的辛劳,也深知父亲在工地上的风吹日晒。他梦想着,通过学习先进的建造技术,未来能让建筑过程更高效、更安全,让更多劳动者能在更好的环境中工作。
喜悦之后,是学费的压力。这个暑假,他投奔了在上海送外卖的舅舅,但没有选择风吹日晒的外卖行业,而是在一家零售店找到收银员的工作。每天下午开始上班,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。
从阜阳到灌南,从灌南到上海,再从上海到江西理工大学,严苏宇的足迹连成一条曲折却始终向上的曲线。
生活给予他离散与粗粝,他却用深夜的坚守,将每一张零钱数对,将每一个单词牢记,将苦难熔炼成攀登的阶梯。收银台后的深夜,不仅承载着他的学费,更托举着一个未来工程师最踏实、最闪亮的梦想——用智慧建造温暖,用技术凝聚家园。
患病父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
周小洲专升本圆梦心仪大学

灌南县田楼镇三兴九组的乡间小路上,三间瓦房静静立在玉米地旁。屋檐下的杂草刚被割过,露出些许泥土——听说助学团队要来,68岁的周良岗撑着腰,慢慢把门口收拾出一块能落脚的地方。“一到下雨天,这儿全是烂泥,没法走。”他拍了拍胸口,眉头皱成一团,“老毛病又犯了,挂水消炎也只能顶一阵,查了有病,也没钱治。”

屋里闷热得很,墙角堆着些旧物,隐约飘着霉味。院子门口的鸭群“嘎嘎”叫着,周小洲站在一旁,寸头利落,眼神却带着股韧劲。这个2003年出生的女孩刚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——专升本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。“要选就选最好的专业。”她说这话时,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谁能想到,这个一心想读好书的姑娘,人生早已刻满坎坷。“没见过妈妈,从小就跟着爸爸过。”周小洲说话间低了低头,声音轻了些,“我刚上大一那年,小一岁的弟弟在河边玩,不小心溺水走了……”

大专三年,周小洲在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日子过得紧巴巴。“学费靠助学贷款,生活费全靠表哥堂哥凑,每个月给几百块。”她说,“在学校打扫宿舍楼楼道卫生,勤工俭学一个月能赚800块,省着点花,够吃饭就行。”原本没想过专升本的她,是被同学拉着报了名,“大一时觉得能念完大专就不错了,同学喊我一起,突然就想再拼一把。”
一旁的周良岗咳了几声,瘦得脱形的身子晃了晃。“我这身体,胃不好,腰也不好,干不了重活,全家靠低保过日子。”他望着女儿,眼里满是愧疚,“她大姑去南京带孙子了,以前还能偶尔帮衬点,现在也顾不上。暑假小洲去灌云她大姐家了,在那儿能省点生活费。”

大专三年靠着一股韧劲熬过来,周小洲的本科梦却卡在了学费上。“9月5号开学,学费要5000元。”她算起这笔账,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,“专科三年贷的款还没还,本科学费又得想办法。”在学校时,她总说“未来走一步看一步”,可真到了眼前,还是忍不住犯愁。
屋檐下的玉米叶被风吹得沙沙响,周小洲眼里重新亮起光:“总会有办法的。大专三年都过来了,这两年本科,我能勤工俭学,能再贷款,一定能读完。”
●郑惠文大一开学费用:7000元
●刘文文大一开学费用:6914元
●严苏宇大一开学费用:6520元
●周小洲大一开学费用:5000元
总值班: 曹银生 编辑: 贾元元
来源: 连云港发布
